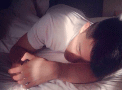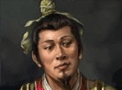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
张晓风
常常,我想起那座山。它沉沉稳稳地驻在那块土地上,像一方纸镇。美丽凝重且深情地压住这张纸,使我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属于我们的历史。
有时是在市声沸天、市尘弥地的台北街头,有时是在拥挤而又落寞的公共汽车站,我总会想起那座山和山上的神木。那一座山叫拉拉山。
11月,天气晴朗,薄凉。天气太好的时候我总是不安,看好风好日这样日复一日地好下去,我决心要到山里去一趟,一个人。一个活得很兴头的女人,既不逃避什么,也不为了出来“散心”——恐怕反而是出来“收心”,收她散在四方的心。
一个人,带一块面包,几只黄橙,去朝山谒水。
车行一路都是山,满山是宽大的野芋叶,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。山色越来越矜持,秋色越来越透明。
车往上升,太阳往下掉,金碧的夕晖在大片山坡上徘徊顾却,不知该留下来依属山,还是追上去殉落日。和黄昏一起,我到了复兴,在日本时代的老屋过夜。
第二天我去即山,搭第一班车去。当班车像一只无桨无楫的舟一路荡过绿波绿涛,我一方面感到作为一个人一个动物的喜悦,可以去攀绝峰,但一方面也惊骇地发现,山,也来即我了。我去即山,越过的是空间,平的空间,以及直的空间。但山来即我,越过的是时间,从太初,它缓慢地走来,一场十万年或百万年的约会。
当我去即山,山早已来即我,我们终于相遇。
路上,无边的烟缭雾绕。太阳蔼然地升起来。峰回路转,时而是左眼读水,右眼阅山,时而是左眼披览一页页的山,时而是右眼圈点一行行的水——山水的巨帙是如此观之不尽。
不管车往哪里走,奇怪的是梯田的阶层总能跟上来。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,他们硬是把峰壑当平地来耕作。我想送梯田一个名字——“层层香”。
巴陵是公路局车站的终点。像一切的大巴士的山线终站,那其间有着说不出来的小小繁华和小小的寂寞——一间客栈,一家兼卖肉丝面和猪头肉的票亭,车来时,扬起一阵沙尘,然后沉寂。
订了一辆计程车,我坐在前座,便于看山看水。司机是泰雅人。“拉拉是泰雅话吗?”我问,“是什么意思?”“我也不知道,”他说,“哦,大概是因为这里也是山,那里也是山,山跟山都拉起手来了,所以就叫拉拉山啦!”他怎么会想起用国语的字来解释泰雅的发音的?但我不得不喜欢这种诗人式的解释,一点也不假,他话刚说完,我抬头一望,只见活鲜鲜的青色一刷刷地刷到人眼里来,山头跟山头正手拉着手,围成一个美丽的圈子。
车虽是我一人包的,但一路上他老是停下载人,一会是从小路上冲来的小孩——那是他家老五,一会又搭乘一位做活的女工,有时他又热心地大叫:“喂,我来帮你带菜!”看他连问都不问我一声就理直气壮地载人载货,我觉得很高兴。
“这是我家!”他说着,跳下车,大声跟他太太说话。他告诉我山坡上那一片是水蜜桃,那一片是苹果“要是你三月末,苹果花开,哼!”这人说话老是让我想起现代诗。
车子在凹凹凸凸的路上往前蹦着。我不讨厌这种路——因为太讨厌被平直光滑的大道把你一路输送到风景站的无聊。
“到这里为止,车子开不过去了,”约一个小时后,司机说,“下午我来接你。”
我终于独自一人了。独自来面领山水的对谕。一片大地能昂起几座山?一座山能涌出多少树?一棵树里能秘藏多少鸟?鸟声真是种奇怪的音乐——鸟越叫,山越深幽深寂静。
流云匆匆从树隙穿过。“喂!”我坐在树下,叫住云,学当年孔子,叫趋庭而过的鲤,并且愉快地问它:“你学了诗没有?”山中轰轰然全是水声,插手寒泉,只觉自己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。而人世在哪里?当我一插手之际,红尘中几人生了?几人死了?几人灰情灭欲大彻大悟了?记得小时老师点名,我们一举手说:“在!”当我来到拉拉山,山在。
当我访水,水在。
还有,万物皆在,还有,岁月也在。
转过一个弯,神木便在那里,跟我对望着。
心情又激动又平静,激动,因为它超乎想象的巨大庄严,平静,是因为觉得它理该如此,它理该如此妥帖地拔地擎天。它理该如此是一座倒生的翡翠矿,需要用仰角去挖掘。
往前走,仍有神木,再走,还有。这里是神木家族的聚居之处。
11点了,秋山在此刻竟也是阳光炙人的。我躺在树下,卧看大树在风中梳着那满头青丝。
再走到那胸腔最宽大的一棵,直立在空无凭依的小山坡上,它被火烧过,有些地方劈剖开来,老干枯乾苍古,分叉部分却活着。怎么会有一棵树同时包括死之深沉和生之愉悦?那树多像中国!中国?我是到山里来看神木,还是来看中国的?坐在树根上,惊看枕月衾云的众枝柯。我们要一个形象来把我们自己画给自己看,我们需要一则神话来把我们自己说给自己听:千年不移的真挚深情,阅尽风霜的泰然壮矜,接受一个伤痕便另拓一片苍翠的无限生机。
在山中,每一种生物都尊严地活着,巨大悠久如神木,神奇尊贵如灵芝,微小如阴暗岩石上恰似芝麻点大的菌子,美如凤尾蝶,丑如小蜥蜴。甚至连没有生命的,也和谐地存在着,石有石的尊严,倒地而死无人凭吊的树尸也纵容菌子、蕨草、藓苔和木耳爬得它一身,你不由觉得那树尸竟也是另一种大地,它因容纳异己而在那些小东西身上又青青翠翠地再活了起来。
忽然,我听到人声。司机来接我了。
山风野水跟我聊了一天,我累了。
回到复兴,第二天清晨我走向渡头,我要等一条船沿水路带我到石门。一个农妇在田间浇豌豆。打谷机的声音不知从何处传来,我坐在石头上等船。
乌鸦在山岩上直嘎嘎地叫着,羽翅纯黑硕大,华贵耀眼。它们好像要说的太多,怆惶到极点反而只剩一声长噫:“嘎—”船来了,但乘客只我一人,船夫定定地坐在船头等人。
我坐在船尾,负责邀和风,邀丽日,邀偶过的一片云影,以及夹岸的绿烟。
没有别人来,那船夫仍坐着。两个小时过去了,我付足了大伙儿的船资,促他开船。
山从四面叠过来,一重一重地,简直是绿色的花瓣——不是单瓣的那一种,而是重瓣的那一种——人行水中,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觉,那种柔和的、生长着的花蕊,你感到自己的尊严和芬芳,你竟觉得自己就是张横渠所说的可以“为天地立心”的那个人。不是天地需要我们去为之立心,而是由于天地的仁慈,他俯身将我们抱起,而且刚刚好放在心坎的那个位置上。山水是花,天地是更大的花,我们遂挺然成花蕊。
回首群山,好一块沉实的纸镇。我们会珍惜的,我们会在这张纸上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。
我们所有的人,都拖延着不去生活,老是梦想着天边一座奇妙的珠瑰园,却偏偏不去欣赏今天就开放在我们窗口的玫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