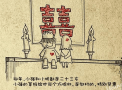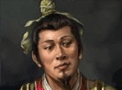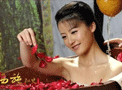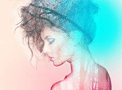尺素寸心
《听听那冷雨》
余光中
接读朋友的来信,尤其是远自海外犹带着异国风云的航空信,确是人生一大快事,如果无须回信的话。回信,是读信之乐的一大代价。久不回信,屡不回信,接信之乐必然就相对减少,以致于无,这时,友情便暂告中断了,直到有一天在赎罪的心情下,你毅然回起信来。蹉跎了这么久,接信之乐早变成欠信之苦,我便是这么一位屡犯的罪人,交游千百,几乎每一位朋友都数得出我的前科来的。英国诗人奥登曾说,他常常搁下重要的信件不回,躲在家里看他的侦探小说。王尔德有一次对韩黎说:“我认得不少人,满怀光明的远景来到伦敦,但是几个月后就整个崩溃了,因为他们有回信的习惯。”显然王尔德认为,要过好日子,就得戒除回信的恶习。
可见怕回信的人,原不止我一个。
回信,固然可畏,不回信,也绝非什么乐事。书架上经常叠着百多封未回之信,“债龄”或长或短,长的甚至在一年以上,那样的压力,也绝非一个普通的罪徒所能负担的。一叠未回的信,就像一群不散的阴魂,在我罪深孽重的心底憧憧作崇。理论上说来,这些信当然是要回的。我可以坦然向天发誓,在我清醒的时刻,我绝未存心不回人信。问题出在技术上。给我一整个夏夜的空闲,我该先回一年半前的那封信呢,还是7个月前的这封?隔了这么久,恐怕连谢罪自谴的有效期也早过了吧?在朋友的心目中,你早已沦为不值得计较的妄人。
其实,即使终于鼓起全部的道德勇气,坐在桌前,准备偿付信债于万一,也不是轻易能如愿的。七零八落的新简旧信,漫无规则地充塞在书架上、抽屉里,有的回过,有的未回,“只在此山中,云深不知处”,要找到你决心要回的那一封,耗费的时间和精力,往往数倍于回信本身。再想象朋友接信时的表情,不是喜出望外,而是余怒重炽,你那一点决心就整个崩溃了。你的债,永无清偿之日。不回信,绝不等于忘了朋友,正如世上绝无忘了债主的负债人。在你惶恐的深处,恶魇的尽头,隐隐约约,永远潜伏着这位朋友的怒眉和冷眼。不,你永远忘不了他。你真正忘掉的,而且忘得那么心安理得的,是那些已经得你回信的朋友。
有一次我对诗人周梦蝶大发议论,说什么“朋友寄赠新著,必须立刻奉覆,道谢与庆贺之余,可以一句‘定当细细拜读’作结。如果施上了一个星期或个把月,这封贺信就难写了,因为到那时候,你已经有义务把全书读完,书既读完,就不能只说些泛泛的美词”。梦蝶听了,为之绝倒。可惜这个理论,我从未付之行动,倒是有一次自己的新书出版,兴冲冲地寄赠了一些朋友。其中一位过了两个月才来信致谢,并说他的太太、女儿和太太的几位同事争读那本大作,直到现在还不曾轮到他自己,足见该书的魅力如何云云。这一番话是真是假,令我存疑至今。如果他是说,那真是一大天才。
据说胡适生前,不但有求必应,连中学生求教的信也亲自答覆,还要记他有名的日记,从不间断。写信,是对人周到,记日记,是对自己周到。一代大师,在著书立说之余,待人待己,竟能那么周密从容,实在令人钦佩。至于我自己,笔札一道已经招架无力,日记,就更是奢移品了。相信前辈作家和学人之间,书翰往还,那种优游条畅的风范,确是我这一辈难以追摹的。梁实秋先生名满天下,尺牍相接,因缘自广,但是20多年来,写信给他,没有一次不是很快就接到回信,而笔下总是那么诙谐,书法又是那么清雅,比起当面的谈笑风生,又别有一番境界。我索来拍写信,和梁先生通信也不算频。何况《雅舍小品》的作者声明过,有11种信件不在他收藏之列,我的信,大概属于他所列的第8种吧。据我所知,和他通信最密的,该推陈之藩。陈之藩年轻时,和胡适、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,名家手迹收藏甚富,梁先生戏称他为man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?朋友之间,以信取人,大约可以分为四派。第一派写信如拍电报,寥寥数行,草草三二十字,很有一种笔挟风雷之势。只是苦了收信人,惊疑端详所费的功夫,比起写信人纸上驰骋的时间,恐怕还要多出数倍。彭歌、刘绍铭、白先勇,可称代表。第二派写信如美女绣花,笔触纤细,字迹秀雅,极尽从容不迫之能事,至于内容,则除实用的功能之外,更兼抒情,称典型。尤其是夏志清,怎么大学者专描小楷,而且永远用廉便的国际邮简?第三派则介于以上两者之间,行乎中庸之道,不温不火,舒疾有致,而且字大墨馆,面目十分爽朗。颜元步、王文兴、何怀硕、杨牧、罗门,都是“样板人物”。尤其是何怀硕,总是议论纵横,而杨牧则字稀行阔,偏又爱用重磅的信纸,那种不计邮费的气魄,真足以笑傲江湖。第四派毛笔作书、满纸烟云,体在行草之间,可谓反潮流之名士,罗青属之。当然,气魄最大的应推刘国松、高信疆,他们根本不写信,只打越洋电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