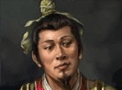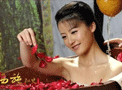因为门德尔松
三月风
晓舟
一个30岁还要来写诗的人,必定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。这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,但我知道与生活有关系,与生命有关系。
那天在地铁站时,我听到了门德尔松的E小调,便下意识地摸了摸左手的四个手尖……什么也没有,光滑的,那些茧子都消失了,没有痕迹。谁也看不出我曾拉过琴,一天八个小时,从漫长的运弓开始,空弦,全弓,一下一下,那琴像只永远杀不死的鸡,它叫啊叫地从G弦叫到E弦,然后再“叫”回去。一天天,我知道了音乐离我有多么远……门德尔松还在响,我无法躲避他流畅的清纯,像我无法躲避失败……我接着学会音阶、换把、顿弓、跳弓,知道泛音的位置,怎么揉弦。从开塞拉到顿特,几年的光阴都被那些蝌蚪一样的音符给吞吃了。我被音乐家这个巨大的幻觉支撑着。
后来,我带着琴去了北大荒。那么广袤的田野更需要一双结实的手。我不能对贫下中农说关于手和帕格尼尼的话题。夏天铲地,秋天割麦,冬天把冻实的粪刨开,我的手再按到指板上时听到琴弦沉重结实的声音,它们少了些灵活,不听命于自己。慢慢的,再看到那把琴时觉得它像一个具体的梦。
门德尔松的E小调也像梦……艺术在某个时期是奢侈的。当我在打麦场上重复着扬场的动作而记起《引子与回旋》的旋律时,我轻声哼着,在节奏中举起木锨,看着饱满的籽粒散开落下,再扬起再落下,一时体会到想象的生活离我们是多么遥远。
门德尔松还在行进着,不必担心有样板戏的乐段插进来……一个傍晚我被叫出宿舍,冷面人对我说:夹上你的琴,去团部报到,排练样板戏,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革命任务,明天就去。回到宿舍先把那琴取下来,擦抹了一遍,琴弦松着,上紧的时候,我听到琴箱中嗡地一声,像是醒来的哈欠。弦对准了,放下琴,我看了看自己的手,依旧有茧子,只是那玩意儿已从指尖换到了手心。
《智取威虎山》中,打虎上山一场有很长的前奏,十六分音符快而密集。这威猛的乐段当然不是一把小提琴就可胜任的,因陋就简,所有的乐器都入了进来,演奏时我仿佛听到零乱溃散的队伍从空中逃过。除了竭力的无奈外,没有音乐。说这不行,可能所有的乐器都要从音阶练起。没有人理会,一支要在11天时间中排出一部大戏的队伍完全有理由不听什么练习曲这套话。戏排出来了,这是一种情感的奇迹。
门德尔松变幻着,愈加明丽,摇曳……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门德尔松的。那天演出后休息,我在一棵柳树下先拉着练习曲,感觉手指已恢复如前。我试着拉起门德尔松,那样地投入,像个又看到希望的人。来视察的宣传股长听到了,他问:你这个手提琴(他一直把小提琴叫手提琴)拉的是什么调调?我回答了。他问:门德尔松是什么人?我回答了。他说,怨不得呢!听着像资产阶级酒吧间里的臭调调。闲了为什么不拉打虎上山?为什么不拉痛说革命家史,江河水?闲了学学二胡,那玩艺离人民近。
他提到了二胡和人民,那样正义。我无话。收起琴时,我看着那琴僵直地躺下,像被收殓的尸体。
从那一天起,我开始记日记了,每天在上铺的角落,将存积在心里的东西写出来,不管多晚,哪怕只有一行,我要写。我开始迷恋那张可以安放心情的白纸,那些文字甚至比音符更能安慰我,它们无声,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。在快写完一本时,日记被一个上海知青偷看了,他在日记本中夹了一张字条:“看完你的日记非常感动,你说了好多我想说的话,希望你把日记坚持写下去,只是不要写得太露。此致,革命的敬礼!知名不具。”
想起来他该是读我文字的第一人,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。我知道他说的太露是什么意思。这之后我有时用诗的形式来记日记,我只记一种心情,那时我曾写出过:风,凛冽的白发。这种现在看来极为做作的句子。
我以一种完全的自觉开始了写作。这不同于拉小提琴,写作没有乐谱可以参照,我也从来没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把写作和生活连在一起。更多的是交谈,与一张白纸对话,每次把一些文字从心里交出来时,那种自话自说的语流很能打动一个想说什么而又无法说出的人。就这样一直写到离开了北大荒。
现在看那只是一个开始。这一开始确实与放弃小提琴有关,但我至今也不能承认就是那个事件决定了我现在的道路。
1977年我回到了北京,25岁。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在等着我。实际上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,我3年的时间我一直为过那种安稳平常的生活而努力着。3年过去后,我回到了写作,全身心地进入,那种迷恋的程度使熟悉我的人都疑惑。我曾在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中说到:一个30岁还要来写诗的人,必定有其迫不得已的原因。这原因一直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,但我知道与生活有关系,与生命有关系。我愿意接受一种说法:写作的人命定了要去写作,不论经历什么样的生活他都会这样。
十几年过去了,诗歌进入了生命,选择了她,我至今唯有感恩。
在走出地铁的时候,门德尔松消失了。想到艺术,突然觉出她从来就没有停顿过,也不会被什么事件所中断,就像此时,左手的指尖没有了茧子,右手握笔的地方却长出了肉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