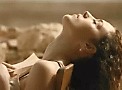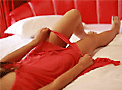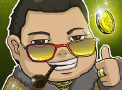艺术的来源是消遣
德国德累斯顿的地标性建筑,是位于易北河畔的圣母大教堂。德累斯顿最大的博物馆是奥古斯特二世建成的茨温格尔宫。教堂也好,皇宫也好,皆是巴洛克式建筑,墙壁、塔身,已被岁月烟熏火燎成黑色,似有千百年的历史。但同行的德国朋友告诉我,皆是假的:1945年,盟军的大轰炸几乎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,这些建筑皆是战后重修的。
茨温格尔宫拥有许多珍贵的藏品,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、拉斐尔的画、鲁本斯的画。拉斐尔的《西斯廷圣母》,是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圣母、圣子,皆望着远方,心事重重,神情忧伤,虽不同于《十字架上的基督》的悲怆,或《最后的晚餐》般的诡异,却也让人或更让人怦然心动。但解说员马上说,这画本也不属于他们,是前些年从拍卖会上买来,专门作为镇馆之用的。如此庄严的意境,突然和“拍卖会”联系在一起,令人啼笑皆非之外,也让我马上回到了现实。
这位解说员是位中年女性,也算快人快语。她接着把我们领到一幅鲁本斯的画前,这幅画画的是赫拉克勒斯。但他不是平日的英雄模样,而是喝醉了,旁边虽有人搀扶,却仍步履蹒跚,嘴里嘟囔着什么。酒精把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,或一个人想借酒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,这是千百年来的常态。我正为这幅画感动时,解说员大姐马上又说,这幅画画好后,卖给了当时的一位贵族。这位贵族喜欢动物超过喜欢人,不管这人是常人还是英雄。他对鲁本斯说,要想让他买这幅画,得再给他往画上加12只小动物。鲁本斯为了卖掉这幅画,马上说:“行。”于是,鲁本斯在这画的犄角旮旯处,又加了12只动物。如果解说员大姐不说,我还发现不了这些生灵;一待发现,此画马上显得不伦不类,让人啼笑皆非。
大姐又指着对面的一幅画说,这是刚说的那幅画的翻版,同样是鲁本斯画的。据说另一位贵族看到那幅画,喜欢,又找鲁本斯来画;但他不喜欢小动物,只喜欢上边的人,于是这些小动物便不见了。这位贵族还不喜欢赫拉克勒斯裸体上遮挡的白纱,想换成红纱,于是鲁本斯真把那白纱画成了红纱。
大姐又带我们走到一幅不知名画家的画作前,说这幅画本来是画一位年轻女人和一个孩子,待年轻女人画出后,一位贵族看这女子长得漂亮,便说,别画孩子了,画我,让她坐在我腿上。于是女子便坐在了这位贵族腿上。但从画上看,这位贵族长得实在太难看了,神似武大郎,这便应了中国一句老话,“鲜花插在了牛粪上”。本来他们身侧的另半面画布上,还画着日常的生活场景,有当时的桌椅板凳和盘子、碗。另一位贵族看到这幅画,也喜欢,但他喜欢的不是人,而是另一侧的盘子和碗。于是他便对第一个贵族说,你喜欢人,我喜欢盘子和碗,干脆,各出一半钱,一分为二。于是一刀下去,一幅画成了两幅画。只有画人的半边饱经岁月沧桑留了下来,女子一直坐在丑男人腿上,而另一半画盘子和碗的画则不知哪里去了。
大姐一口气讲完,回头看着我,我有些惶恐。她接着说了一句歌德式的哲言:“艺术,就是这样,来源于消遣;是时间,把它们变严肃了。”
我半天不敢接话。
出了茨温格尔宫,擦了擦额头上的汗,我深以为然。
作者:刘震云 摘自微信公众号“当代”